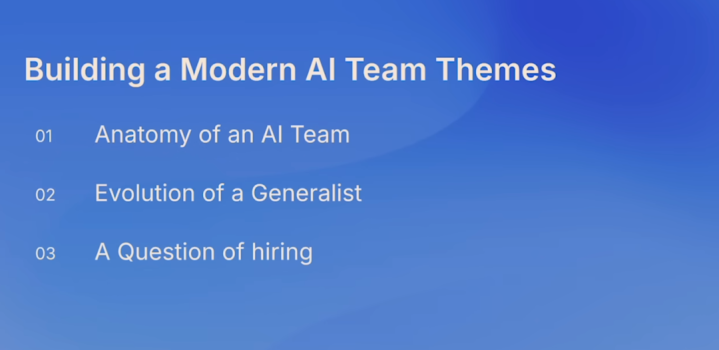如何构建现代化的AI团队: 90%的公司都在犯同一个错误
你是否也曾被高层一句“我们要做AI优先”推上转型前线,却发现预算没变、团队没扩、资源没加?这篇文章将带你复盘AI团队建设中的常见误区,并通过真实案例告诉你:不是每家公司都需要PhD研究员,更重要的是如何用现有资源打造真正能落地的AI能力。
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:公司高层突然宣布”我们现在是AI优先的公司”,然后看着你说”去组建一个AI团队吧”,但预算和人员编制却纹丝不动?如果你点头了,那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从Shopify到Duolingo,再到Zapier,似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在宣布自己转型为”AI优先”,仿佛这是一张通往未来的船票。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:你被赋予了AI转型的重任,却没有额外的资源去实现它。
最近我看到Wisdocs机器学习团队负责人DenysLinkov在一次技术分享中深度剖析了这个问题。他的观点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,因为他不是在谈论那些拥有无限预算的大科技公司如何组建AI梦之队,而是在解决我们这些普通公司面临的真实挑战:如何在有限资源下,通过重新培训、技能提升和团队增强来交付AI转型的承诺。
这不是一个关于招聘最顶尖AI研究员的故事,而是关于如何让现有团队在AI时代重新焕发活力的实用指南。
我深信,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。那些能够巧妙地重构现有团队、培养跨功能AI能力的公司,将在未来几年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。而那些还在纠结是否要花重金挖角顶级AI研究员的公司,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转型窗口期。
AI团队的真实构成:不是你想象的那样
Denys在分享中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精辟的观点: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完全不同的AI团队结构。他将公司分为三大类:技术公司(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)、垂直化解决方案或服务公司(如Palantir和他工作的Wisdocs),以及技术赋能公司(银行、零售商、中小企业等)。这个分类看似简单,但背后蕴含的团队构建逻辑却完全不同。
我发现很多公司在组建AI团队时犯的最大错误,就是盲目模仿科技巨头的做法。看到Google有几千名AI研究员,就觉得自己也需要招聘PhD级别的研究人员;看到OpenAI在模型训练上投入巨资,就认为自己也需要从头开始训练大模型。但现实是,绝大多数公司并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,而是需要学会如何更好地使用现有的轮子。
Denys提到的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:传真机市场至今仍然存在,价值数十亿美元,而且还在增长。2017年,美国只有3%的支付是无接触式的,支票仍然占据着庞大的市场份额。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问世40年后,医疗系统和电子病历才开始数字化。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:技术从来不是限制我们成功的瓶颈,如何使用技术才是。
这个观察让我重新思考AI团队的本质。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能够从零开始训练GPT-4的研究员,而是能够理解业务需求、整合现有技术、并将AI能力转化为实际商业价值的复合型人才。正如Denys所说,90%的人类问题都可以用现有技术解决,关键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技术。
在我看来,这种认知转变具有革命性意义。它意味着AI团队的核心能力不再是算法创新,而是问题定义、产品集成、ROI测量、数据获取、工作流优化、界面构建、产品销售和客户关怀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技能集合,需要完全不同的招聘策略和团队结构。
Denys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:如果让你用五个来自顶级实验室的AI研究员来交换你现有的团队(可能还需要额外付费和选秀权),你会做这个交易吗?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,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因为那些拥有领域知识、了解业务流程、能够与客户沟通的现有团队成员,其价值远超过几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员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:我们为什么会对AI研究员有如此强烈的迷恋?我觉得这partly源于对AI技术的神秘化,partly源于对复杂性的恐惧。我们总以为AI是如此高深莫测,只有PhD才能驾驭,但实际上,在商业应用层面,AI更像是一种新的编程范式,需要的是工程思维而非研究思维。
全才型工程师的崛起:为什么专业化可能是陷阱
Denys在2021年组建第一个机器学习团队时采用的策略让我眼前一亮:他选择招聘全才型工程师(generalists),并通过自动化工具来支持他们。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显得有些另类,因为主流观点一直认为AI需要高度专业化的人才。但回过头看,这种策略显得极其前瞻。
他当时面临的挑战非常具体:需要服务数十万个并发模型,支持多领域应用,成本要低,还要支持实时训练和服务。为了达成这些目标,团队构建了定制的MLOps平台,主要做encoder模型的微调,建立了RAG即服务,并管理着十个微服务中的六个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,但关键在于他们是如何配置人员的。
在模型训练方面,Denys没有追求顶尖的专家,而是设定了一个务实的标准:了解模型的通用架构,能够进行encoder微调,具备一定的数据工程能力,熟悉HuggingFace即可。在模型服务方面,由于他本人有云工程背景,承担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工作,为团队建立了足够的抽象层,让其他成员不需要深入了解Kubernetes或具体的训练服务细节。最重要的是,他特别强调团队成员必须具备与客户直接沟通的能力。
我觉得这种配置策略的聪明之处在于,它认识到了现代AI工作的真实需求。在大多数商业场景中,你不需要发明新的模型架构,你需要的是快速理解客户需求,选择合适的现有工具,并将它们整合成可用的解决方案。这更像是系统集成工作,而非科学研究。
到了2024年,当Denys在新组织中再次组建团队时,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开源工具变得更加成熟,商业模型API变得更加强大,他们的技能需求配置也相应调整。在训练方面,使用商业API、prompt调优和模型微调变得更加重要;在服务方面,由于可以使用开源解决方案,不再需要从头构建平台;在领域知识方面,由于专注于医疗记录处理,对领域专业性的要求反而提高了。
这个演进过程让我深刻理解了全才型工程师的价值。他们不是什么都懂一点的”万金油”,而是能够快速学习新工具、适应变化环境、并在不同技能领域之间建立连接的复合型人才。在AI技术快速演进的今天,这种适应性可能比深度专业化更加重要。
我个人的观察是,AI领域的技术栈变化速度极快。六个月前还是主流的工具,现在可能已经被新的解决方案取代。在这种环境下,那些能够快速学习新工具、理解技术趋势、并将这些工具应用到具体业务场景中的全才型工程师,比那些只专精于某一特定技术的专家更有价值。
Denys提到的内环和外环概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性。内环是团队每天必须完成的核心活动:模型训练、prompting、产品需求理解、模型服务、领域专业知识和商业案例构建。外环是那些能让团队脱颖而出的更广泛活动。如果内环的技术执行能力薄弱,你会在技术实施上遇到困难;如果外环的领域循环薄弱,你将无法找到产品市场契合点。
这种框架让我重新审视了专业化的问题。在AI的早期阶段,当你还在寻找产品市场契合点、尝试基本进展时,你需要的是能够快速试错、适应变化的全才型人才。只有当你在模型训练、服务等方面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,需要提升那最后5%的性能时,才需要引入专家来处理特定的技术瓶颈。
重新定义技能提升:从编程到建构
让我最有感触的是Denys对技能重构的看法。他认为在AI浪潮中,有三个核心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:学会建构(learntobuild)、成为领域专家(becomeadomainexpert)、面向人类工作(behumanfacing)。这三个方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技术技能框架。
“学会建构”不再意味着从头编写代码,而是从静态的产品需求文档转向功能性原型。Denys强调,我们应该告别那些痛苦的对话——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关于”这不在需求里”或”这是个边缘情况”的争执。相反,我们应该通过快速原型来缩短反馈循环,让想法能够快速得到验证或推翻。
我深有同感。在传统的软件开发中,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在文档编写和需求澄清上,但往往到了实际开发阶段才发现很多假设是错误的。AI工具让我们能够快速构建可工作的原型,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看到和体验实际的产品行为,这比任何文档都更有说服力。
在成为领域专家方面,Denys的观点更加激进。他认为领域专家不应该只是提供输入和反馈,而应该直接编写用例、定义需求,并具备直接与LLM工作的能力。这意味着技术和业务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,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一定的AI素养。
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在我接触的很多项目中,那些最成功的AI应用往往来自于深度理解业务场景的领域专家,而不是纯技术人员。因为他们知道哪些问题真正值得解决,哪些解决方案在实际业务环境中可行。而AI工具的普及,让这些领域专家不再需要依赖技术人员来实现他们的想法。
在面向人类工作方面,Denys特别强调工程师必须参与客户沟通。这在传统的技术组织中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,但在AI时代却变得至关重要。因为AI解决方案往往需要大量的迭代和调优,而这种迭代必须基于真实的用户反馈。如果工程师无法直接听到用户的声音,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技术决策。
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:Denys的团队每周都会安排30分钟的学习时间,由团队成员轮流分享新的主题。这种做法看起来可能有些”内卷”,但正如他所说,不这样做的后果会更严重。在AI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,停止学习就意味着被淘汰。
这让我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:在AI时代,持续学习不再是可选项,而是生存必需品。我们已经从年度评估进入了六个月评估的时代,技术的演进速度远超过了传统的学习和适应周期。这要求我们必须将学习内置到工作流程中,而不是将其视为额外的负担。
招聘的新逻辑:上下文比算法更重要
Denys关于招聘的观点让我重新审视了AI时代的人才策略。他认为招聘人员主要有两个目的:持有上下文(holdcontext)和基于上下文行动(actoncontext)。这个简单的框架却蕴含着深刻的洞察。
在传统的技术招聘中,我们往往过分关注候选人的算法能力或编程技巧。但在AI时代,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理解业务上下文,并基于这种理解做出正确的决策。一个能够与客户深入沟通、理解他们真实需求的工程师,可能比一个算法大师更有价值。
Denys提到一个现象让我印象深刻:很多公司仍在使用与工作内容完全无关的LeetCode题目来筛选候选人。这种做法在AI可以轻松解决大部分编程题目的今天,不仅失去了评估意义,而且可能筛选掉那些真正适合AI工作的人才。因为AI工作更多的是关于问题定义、方案选择和系统集成,而不是算法实现。
我特别赞同他对初级工程师价值的分析。当很多公司都在讨论”AI将取代初级工程师”时,Denys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:为什么YCombinator还在为学生和年轻人举办AI学校,吸引2000人前往旧金山?如果初级职位真的没有价值,他们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多资源?
这个观察让我思考一个更广泛的问题:我们是否过于迷信经验和资历?在一个技术快速变化的领域,那些没有太多既定观念、愿意快速学习新工具的年轻人,可能比那些固守传统做法的资深专家更有价值。关键不是你有多少年的经验,而是你能否快速适应新的工作方式。
Denys最终回到了他的”Ampere赌注”:你会选择五个来自顶级实验室的研究员,还是一个拥有领域专业知识、能够销售产品、能够与客户产生共鸣的团队?对于他的公司来说,答案很明确:后者更有价值。
我觉得这个选择反映了AI商业化的本质。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,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集合。在商业环境中,能够快速将技术转化为客户价值的能力,远比发表顶级论文的能力更重要。
预算约束下的团队优化:现实主义的智慧
让我最受启发的是Denys关于预算现实主义的讨论。他非常坦率地承认,作为团队负责人,你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预算。这意味着你必须在模型训练、模型服务和商业洞察这三个维度上做出权衡,决定在每个方面投入多少资源。
这种思维方式与很多AI团队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经常看到一些团队制定宏伟的计划,想要在每个方面都达到行业顶尖水平,但最终因为资源分散而什么都做不好。Denys的方法更加务实:明确定义每个维度的最低要求和最优目标,然后根据实际预算进行配置。
在模型训练方面,他们的标准是”上半部分”的能力:了解通用架构,能够进行encoder微调,具备数据工程技能,熟悉HuggingFace。这个标准既不会太低(避免基本工作都无法完成),也不会太高(不需要能够训练GPT-3级别的模型)。
我觉得这种标准设定的智慧在于它的实用性。大多数商业场景并不需要从头开始训练大模型,而是需要在现有模型基础上进行适配和优化。能够熟练使用现有工具、理解其限制和优势的工程师,往往比那些只知道理论的研究人员更有价值。
在模型服务方面,Denys采用了分层抽象的策略。作为团队负责人,他承担了底层平台构建的复杂性,为团队成员提供了简化的抽象接口。这让其他成员不需要深入了解Kubernetes或分布式系统的细节,只需要理解如何使用这些抽象以及它们的权衡取舍。
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现代软件开发的趋势: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全栈专家,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理解系统的整体架构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。在AI领域也是如此,你不需要每个人都精通底层算法,但每个人都需要理解AI系统的能力边界和使用场景。
最重要的是,Denys在商业洞察方面设定了很高的标准。他要求团队成员能够直接与客户对话,能够理解和传达技术决策的商业影响。这种要求在传统的技术团队中可能显得过分,但在AI商业化的今天却是必需的。
我深刻认同这种资源配置策略。它体现了一种成熟的管理思维:承认约束的存在,并在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解。这比那种无视现实、追求完美的做法更容易成功。
组织学习的新范式:从个人技能到集体智慧
Denys提到的团队学习机制让我看到了AI时代组织能力建设的新模式。他们每周安排30分钟的学习时间,由团队成员轮流分享新主题,涵盖团队和公司的核心优先事项。这种做法看似简单,但背后体现的是对持续学习的深刻理解。
我觉得这种学习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传递,更在于文化建设。它向团队成员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:在AI时代,学习不是可选的额外活动,而是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当学习成为团队日常节奏的一部分时,它就不再是负担,而是自然的工作方式。
这让我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:在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,个人知识的半衰期正在急剧缩短。六个月前学习的AI工具可能现在已经被更好的替代方案超越,一年前的最佳实践可能现在已经过时。在这种环境下,比掌握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的能力。
Denys强调的”世界变化太快”不是夸张,而是客观现实。他提到现在使用的是六个月而不是一年的评估周期,这个细节虽小,但反映了整个行业节奏的加速。这种加速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,也体现在商业模式、用户期望和竞争格局的变化上。
我认为这种组织学习机制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。在传统的技术团队中,知识往往集中在少数专家手中,其他人只能被动接受。但在AI时代,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一定的AI素养,都需要能够独立做出技术决策。通过轮流分享的机制,每个团队成员都有机会成为某个领域的”专家”,这种角色轮换有助于培养每个人的综合能力。
从更广的角度看,我觉得这种学习模式体现了AI时代组织能力的新特征:不再是金字塔式的知识传递,而是网络式的知识共享。每个节点(团队成员)都既是知识的消费者,也是知识的生产者。这种模式的适应性和韧性远超传统的层级式组织。
技术决策的哲学:实用主义vs完美主义
通过分析Denys的整个分享,我发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:实用主义。无论是技能配置、团队结构还是招聘策略,他都优先考虑”够用”而不是”完美”。这种思维方式在AI时代尤其重要,因为技术的变化速度使得追求完美往往意味着错过机会。
他的90%技术理论特别能说明这一点:我们已经拥有解决90%人类问题所需的技术,限制我们的不是技术能力,而是应用能力。这个观察打破了技术行业普遍存在的”技术崇拜”,提醒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更好地使用现有技术,而不是发明新技术。
我觉得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在AI商业化的当下尤其重要。很多公司被AI的技术复杂性所intimidate,认为必须投入巨资研发才能参与这场革命。但实际上,大多数商业价值来自于对现有AI能力的巧妙应用,而不是技术突破。
Denys关于不同公司类型需要不同策略的分析也体现了这种实用主义。技术公司可能需要投资基础研究,但大多数垂直化和技术赋能的公司更需要的是集成和应用能力。认清自己公司的定位和需求,比盲目跟风更重要。
这种实用主义还体现在他对专业化的态度上。他并不反对专业化,但他认为专业化应该基于实际需求,而不是理论完美。当你的团队还在寻找产品市场契合点时,全才型工程师的适应性比专家的深度更有价值。只有当你需要提升那最后5%的性能时,专家才变得必要。
我个人非常认同这种哲学。在AI技术快速变化的环境下,那些能够快速适应、务实决策的团队往往比那些追求技术完美的团队更容易成功。这不是说技术质量不重要,而是说我们需要在质量和速度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。
AI团队的未来:从技术导向到价值导向
综合Denys的分享和我自己的观察,我认为AI团队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:从技术导向转向价值导向。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技能的定义,也改变了我们对成功的衡量标准。
在技术导向的时代,团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算法的先进性、模型的复杂度或系统的性能指标上。但在价值导向的时代,团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解决的问题数量、创造的商业价值或用户满意度上。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”好的”AI工程师。
我觉得这种转变的背景是AI技术的商品化。当基础AI能力变得increasinglyaccessible时,差异化就不再来自于技术本身,而来自于如何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中。这就像互联网技术在早期需要专门的网络工程师,但现在任何开发者都可以轻松构建网络应用一样。
从招聘角度看,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”AI专家”,而是具备AI素养的业务专家或具备业务理解的AI从业者。这种复合型人才能够在技术可能性和商业需求之间建立桥梁,这正是AI商业化的关键。
从团队结构角度看,这意味着AI团队不能再是孤立的技术团队,而必须与产品、销售、客户服务等其他部门深度集成。Denys强调的”人类面向”能力正是这种集成的体现:AI工程师必须能够直接与客户对话,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点。
从组织文化角度看,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学习文化,让每个人都能够跟上技术的变化。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AI专家,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理解AI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以及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效利用AI。
我预测,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像Denys这样的AI团队负责人,他们不会被技术的复杂性所overwhelm,而是专注于如何将AI技术转化为实际的商业价值。这些团队将成为企业AI转型的真正推动力,因为他们理解技术,但更理解业务。
写在最后:务实的AI转型之路
听完Denys的分享后,我最大的感悟是:AI转型不是一场技术革命,而是一场管理革命。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AIPhD,而在于你能否重新组织现有资源,让他们在AI时代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
对于那些被赋予AI转型任务但没有额外资源的团队负责人,我觉得Denys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:不要试图复制大科技公司的做法,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策略。重要的是理解你的瓶颈在哪里,你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组合,以及如何在有限预算下实现最大价值。
我特别认同他关于持续学习的强调。在AI技术快速变化的今天,停止学习就意味着被淘汰。但学习不应该是个人的负担,而应该成为团队文化的一部分。通过建立定期的知识分享机制,让学习成为团队日常工作的自然组成部分,这样才能确保整个团队的竞争力。
从更宏观的角度看,我认为Denys的分享揭示了AI时代组织管理的一个核心矛盾:技术变化的速度与组织适应速度之间的gap。那些能够缩小这个gap的组织将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,而那些无法适应的组织将被时代抛弃。这不是危言耸听,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最后,我想回到Denys提出的那个根本问题:技术是否是限制我们成功的瓶颈?答案往往是否定的。真正的瓶颈通常在于我们如何组织人员、如何定义问题、如何衡量价值,以及如何适应变化。AI技术给了我们强大的工具,但工具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使用者的智慧。
对于正在面临AI转型压力的团队负责人,我的建议是:不要被技术的复杂性吓倒,也不要被预算的限制绊住。从重新定义现有团队成员的角色开始,让他们在AI时代找到新的价值定位。投资于人的成长和适应能力,建立学习型的团队文化,这些投入的回报往往超过任何技术投资。
AI的未来不属于那些拥有最多PhD的公司,而属于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将AI能力转化为客户价值的公司。而这种转化能力,正是通过像Denys这样务实的团队建设方法来实现的。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我们都需要成为既懂技术又懂业务、既能编程又能沟通、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复合型人才。这不是更高的要求,而是时代的基本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