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自跨文化千禧一代的作家之声:刘倩和她的《别来春半》
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正在走上各行各业的舞台。3月29日,零零后旅美青年作家刘倩带着她的首部虚构散文集《别来春半》做客可一书店,以“在离散与回归之间,寻找千禧一代的华语文学之声”为主题与《钟山》资深编辑汪楚红展开对话,并接受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的采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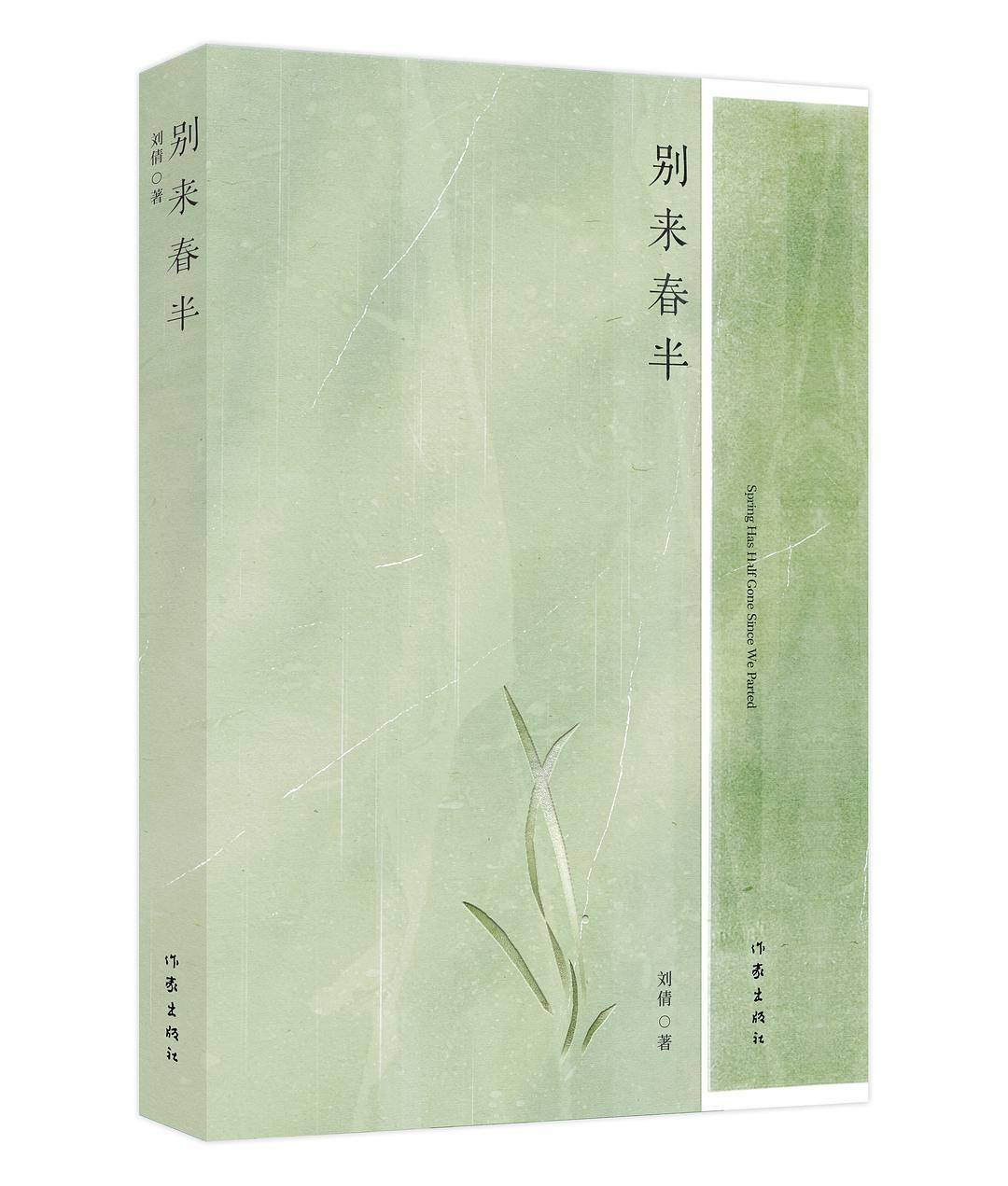
刘倩成长在信息大爆炸的年代,又有着跨文化生活体验,其本人又是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,多种元素的影响使得她的作品既有古典文化的底蕴,又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,《别来春半》首章中的作品里,就收录了不少她高中及本科时期,就一些经典的文学意象进行的现代再演绎。这其中不乏文笔稚嫩的文章,但也多少反映出了年少时更为天真烂漫的心境,显然有别于现在更为沉重深刻的创作动机。她学习过很多种外语,日常学习、生活频繁的使用外语,但她一直坚持使用中文写作,“在美生活多年,中文不再只是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存在,而是我个人及文化身份的一部分,也是我用以抒发见闻感想、跨越不同文化与语境的坚实桥梁。坚持中文创作,讲述中国人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故事,一是提醒自己的文化根基从何而来;二是希望能够将自己学贯中西的经历与感受分享给更多人,尽可能地在博大的中文语境里‘府纳百家’。”
当前刘倩的创作围绕“流浪与离散”、“跨文化语境”以及“个人身份认同”等主体,她认为任何跨文化写作绝不等同于对于母语文化的摒弃或是叛逃,“跨文化写作是对自我真实声音的一种肯定。它指引着我去不断思考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、对话,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如何不断寻找和尝试定义的文化、乃至家国记忆的边界线。在世界文化交融频繁的今日,守护语言文化的方式之一便是走向世界,寻找新的途径和方式将它带到世界的舞台上。写作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为了铭记,而身处异国他乡,只觉得这样的使命感更加强烈。”

千禧一代的文学自觉
如今的文坛,六零后依然有旺盛的创作力,七零后在冲击各大奖项,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,刚刚走入主流文坛视野的零零后作家又在发出怎样的声音?
刘倩提出,对于自己这样千禧一代的有着跨文化生活背景的写作者来说,写作的倾向已经与前辈有了很大不同,“我认为许多优秀的前辈作家们,尤其是身处二十世纪时代变动的创作者,往往因为受到动荡时代的大环境影响,在书写个人与家国情怀之间关系时,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渲染读过许多这类的故事,有时会感觉人物被历史的巨轮碾过,或成为某个时代一角的缩影,但往往其微小的命运与社会的存亡相辅相成,难以有‘较为独立’的个人叙事色彩,诚然,我的观点并不绝对,只是出于一个偏‘离散与回归’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中的特色之一,这也恰恰是许多读者为之津津乐道的写作亮点,但放眼当今全球化的变革和世界文化的交汇,我认为华语写作的方向逐渐走向了更加广阔、多元的一片天地,当然因此在风格和特点的塑造上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”
时代在变化,写作者的生活经验在变化,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变化,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来说,“未完成性”是千禧一代作家的特质,“比起塑造一个个被时代所推动、影响,打造的故事,我希望更多聚焦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去拷问、挑战,甚至是引领时代的思潮,赋予写作、以及角色本身更多的‘个人主动权’,企图走出时代本身框定的局限性——这既是新生代作者的机缘,也是挑战,我期待看到更多优秀的新生代作者创造出不一样的华语文学风景。”
今年,刘倩的新作《她从此不敢扮观音》即将面世,这是一部聚焦海外底层女性生活经历的短篇小说集,“我希望通过小说虚构的形式,来探讨被社会边缘化的特定女性群体,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冲突、身份认同与生存困境。虽然她们的故事、生活轨迹,以及所背负的时代承重往往被主流叙事忽略,但她们的挣扎与坚韧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瞬息万变的复杂性。我希望继续通过写作,让更多这样的声音被大众所知悉、听见。”而关于标题中“观音”这个概念,她解释到这是想要引入具有神性色彩的意向,希望能启发读者去思考人物和宿命、以及生命哲理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故事中角色的执念、越是想抓住的人与事,在企图扮演超出自我生命载体的庞大意象过程中,可能结果往往不尽人意。“在新一部的作品中,我希望可以颠覆读者的预期,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。”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校对 盛媛媛